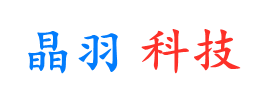电影剧情有一个女钢琴老师「解析」
这个文本的主要情节是这样一个连接:母亲—女儿埃里卡—情人克雷默尔。
这很清晰地显示了某种三角关系的叙事结构,而处于叙事顶点的是母亲。文本开篇开宗明义的一句话:“母亲,被人一致公认为是在国家生活和家庭生活中集中世纪异端裁判所的审讯官和下枪决命令者于一身的人物。”
在文本叙事的三分之一处,作者就将父亲迅速宣告死亡,即“她父亲在完全神志不清的情况死在施泰因霍夫”,这是一个精神病院。因为父亲“眼神近乎失明”又“日趋恶化”,且“完全认不清方向、已经糊涂了”。父亲叙事的迅速终结,腾出了大量的空间来叙述共生体般的母女关系。
比如那张夫妻的床腾出来,母亲要求埃里卡与自己睡在一起,在夜里也要监督着她。后来克雷默尔冲进她家指着那张床说:“这是那对‘夫妻’的,埃里卡和母亲的”,而母亲却害怕给埃里卡一张床。“母女”成为“夫妻”,这样的叙事细节预示了某种畸形的关系。
在同一张床上,一次母女的激烈争吵后,埃里卡爬在母亲的身上像性行为式的亲吻纠缠,母亲反抗着,她压制着母亲,这是她的某种反抗:“仿佛在一场性爱战斗中,目标不是亢奋的情欲,而是母亲本身,母亲这个人”。像是在这场争斗中,埃里卡近乎报复般地强奸了母亲一样。对此,聚焦埃里卡的童年与青春期的性压抑成长过程成了最迫切的问题。
对于性成熟的埃里卡,不仅母亲压抑着,外祖母也加入进来:“她们扑到每个男人面前,使男人无法靠近她们的幼鹿并在她身上得手”、“苍鹰的母亲和鹫的祖母不准由自己照料的幼鸟离开鸟巢”。
文本中对母亲强势的形容词有“狮子般的”、“美洲母狮”,而埃里卡则是“绵羊”。埃里卡要面对的是“强权与压抑,猎者与猎物之间的根深蒂固的秩序”。前者是母—女关系,后者是埃里卡—克雷默尔的关系。在年龄上,埃里卡比克雷默尔大很多。这是年老的女性与年轻的男性之间的性叙事,它试图颠覆年老男性与年轻女性之间的传统性叙事模式。因此理解母女畸形共生的关系是梳理后者关系的前提。
当埃里卡试图与一名大学生来往时,这是青春期时埃里卡第一次溢出母女关系,但旋即就被母亲禁足。同时,“只要孩子一同男人见面,她就用打死她来进行威胁。母亲坐在瞭望塔上监视、寻觅、推算,得出结论和进行惩罚”。
于此,母亲发现了一种权力,“自从母亲第一次发现权力以来,她一直喜爱权力”。母亲试图占据家庭中男权的话语中心,她特别希望“她的孩子宁愿拴在母亲的裤带上,也不在性爱激情的锅里煨熟”。这是母亲抵制男权社会的宗旨,她希望女儿对男性以性冷淡来抵制,埃里卡最初也是这么对待克雷默尔的。
米利特认为这种“至今仍然普遍存在的性冷漠很可能出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对妇女严厉的限制使她们对性产生了恐惧和厌恶”。正是母亲对埃里卡残忍的监督,她形成了对性的恐惧:“下身和恐惧是她的两个友好的同盟者,他们几乎总是一起出现”。这种权力中的训练、监视、惩罚等手段的运用,是家庭内部母亲对女儿运用的规训权力。她考虑女儿正常与不正常的规训问题的起点是“母亲警告她……宁可要艺术的顶峰,也不要性的堕落”。
这就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所研究的家庭内部的母亲对女儿实施的“全景敞视主义”。母亲对埃里卡进行全天候的监视,形成“精神对精神的权力”,监视不到的地方,用疯狂地给女儿打电话的方式予以覆盖。
在叙事中,为了强调埃里卡渴求的自我主体性,文本中的“她”字用大一号的字体书写,文本印刷的时候,“她”这个字被放大、加黑、加粗。这样的方式显得“她”这个字在一个语句中特别突兀。作者用这样的方式向读者传达着某种压抑的情绪。
比如:“她……因为回家太晚,几分钟后自己将要在母亲的切割烧嘴的烈焰之下烧成一堆灰”。
这种大写也强调着她与母亲之间关于自我的争夺。但她的自我一直被母亲压抑着,即“这只昆虫已丧失了自己爬行的技能。埃里卡被放进了永恒的烘烤用的模子里去烘烤”。
当表弟探望处于青春期时的埃里卡,她第一次将性的压抑以及某种虐恋倾向投射到了表弟身上,第一次将表弟当成是性幻想的对象。表弟肆意的游泳与年轻的姑娘调情,而埃里卡的青春只能被母亲箍在练琴上。音乐对于埃里卡的母亲来说,是她从劳动阶层爬上艺术家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可以使母亲“不断赚取金钱”和声誉,也正是“埃里卡从小就被装进这个乐谱体系中。这五条线控制住了她。自从她会思考起,她只能想这五条黑线,别的什么都不能想。这个纲目体系与她母亲一道把她编织进一个由规定、精确的命令和规章构成的撕不开的网中”。
文本自始至终的“钢琴”意象是母亲权力意志的投射,我们并没有发现埃里卡的兴趣究竟是什么。就像劳伦斯《儿子与情人》中保罗的绘画对于他母亲来说只在乎是否能转换成金钱。埃里卡的钢琴也是这样。
这样的压抑把埃里卡打造成一个钢琴教师,而也正是埃里卡被规训的音乐成就,克雷默尔才成为了她的学生,并似乎对埃里卡展开恋爱的追求。这样的叙事很有意味,它在一个压抑的框架里形成了某种生产性的要素:钢琴,即可以溢出母女共生体的要素却恰恰是一直压抑她的。钢琴具有了双重属性,一对相斥的要素。正是这样,处在对撞中心的埃里卡才会感到异常痛苦。钢琴是母亲意志的拟人化,而在埃里卡最排斥的地方生长出一个情人。以这样的方式撕扯着埃里卡。
我们可以想象,克雷默尔这种追求起初或许也是纯洁的,这种追求比他大二十多岁的埃里卡是否存在着弗洛伊德式恋母情结呢?但他并不知道埃里卡音乐成就的背后隐匿着巨大的性压抑与反抗母亲权力的张力。这种张力弥漫在文本中各处,造成了读者强烈的阅读窒息感。
比如埃里卡必须与母亲睡在一张床上,母亲注意着她的手防止她的自慰。为了反抗母亲控制的野心,埃里卡用父亲留下的刀片切割自己的手背和生殖器,去桥洞下阴暗小屋里观看色情表演,用望远镜凝视着男男女女的游人,直到作者用漫长的篇幅叙述埃里卡窥视谷底草地中土耳其男人和一个老女人性行为激烈而野蛮的场面,“对于女旁观者来说这情境产生的效果是毁灭性的”。
作者故意叙述成动物性的不带任何情感的直接繁衍式的场面,将人性的神圣性拉回到动物性。这大篇幅的叙事是埃里卡的一次性压抑的转移,她产生的尿急的生理反应并且在草丛中释放,似乎像是自己也经验了一次性经历。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观看权力的主语通常是男性,埃里卡试图在这些男性主导的性权力的地方掌握主动权,包括后来的受虐信也是试图在男女两性中掌握主动,借此对畸形母权的性压抑的主动溢出。
埃里卡故意用打碎的玻璃片放在自己年轻女学生衣服口袋里,使得她的手划伤,不能表演钢琴。埃里卡给出的解释是“她已经这么大了,可以用经验代替青春”。埃里卡用切碎其他年轻女孩的青春来报复自己逝去的青春。
作者在文本中处处强调着“没有什么改变得了这该死的区别:衰老/年轻”。年老就是埃里卡认定自己的唯一缺点。青春耗尽在压抑的学习与母亲的规训中,于是“在母亲和孩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复仇比赛”,终于,埃里卡溢出这段关系的最终努力凝聚在了一封给自己的学生克雷默尔要求虐恋的一封信。
对于这样超出克雷默尔理解的要求,他们之间的年龄、经历、职业身份等一切的差异巨大,这种差距也压抑着他。在这对关系中,埃里卡变成强势的一方,克雷默尔是弱势的。面对这种压抑,他试图用一个简单的“老”字来概括这一切,试图理解他的钢琴老师要求的这一切。在性上,他也想打破牢固的师生关系的身份,他讨厌着年龄差距,他想敲碎这个女教师拘谨、羞怯、克制的表象。
在埃里卡的面前,是年龄带来的压抑。在克雷默尔面前,是职业身份带来的压抑。于此,他想“把她当学生,至少一周有一次”,他渴望着揭开这身份,“让她纯洁的肉体显露出来”。总之,克雷默尔也产生了报复的心理。
于是,埃里卡和克雷默尔的性叙事在作者的叙述下变成了一场战争,是支配与反支配、控制与反控制的争夺占有权力的战争,比如“她厚颜无耻的书信进攻”、“克雷默尔开始了新一轮的带有严肃意图的攻势”这种军事词汇式的描述。
他显然意识到了他的老师扭曲的心理,常年的性压抑堵塞了她正常的情欲表达,他质问埃里卡“你这些年怎么能忍受你母亲的”。在他第一次追到埃里卡家中并读完了那封信后,他其实并不理解她多年的性压抑所克制的人格究竟是什么?
他不理解她的信只是幌子,那是她多年来对自己性压抑的某种弗洛伊德升华式的释放。但她其实希望信中的一切都不要发生,这是她隐匿在那封虐恋的信背后的渴望,即“出于爱一切都永远未曾发生”。这是埃里卡的某种策略,她拒绝被动。但这也是埃里卡因性压抑变得精神分裂和双重人格的某种体现,她想要的与她表现的表里不一。波伏娃在《第二性》里认为“任何教育也不能阻止女孩子意识到她的身体。至多只能强加给她严格的压抑,这种压抑随后要成为她的性生活的沉重负担”。
在克雷默尔侵入到母亲的领地后,这位“家庭女财政部长”认识到“这是权力的移交和换岗”。而埃里卡试图“把这个过去一直为母亲占有的意志现在像接力赛跑中的接力棒一样交给了克雷默尔”。多年以来,“学习要求她保持理智,母亲则要求她服从”。她渐渐地将自我的主体性交给母亲,按照母亲的方式与愿望规训自己,文本中用“献身于母亲的愿望”来形容。
这种“桎梏是埃里卡自己决定的,她决心让自己成为一个物体,一个工具”。她“经过良好驯化的服从能力”最终坍塌成了一封虐恋信。李银河的《虐恋亚文化》中认为受虐者的逻辑是“通过彻底的屈从是为了得到权力,通过服从得到对方的爱和关注,同时也就占有、掌握、控制了对方,使对方不能摆脱自己的束缚……实际上是施虐者受到受虐者的束缚……屈从者的真正动机乃是权力。”(这个策略亦是洛丽塔对亨伯特运作的。)
在受虐信之前,埃里卡对年轻的克雷默尔总是“希望控制他和他的欲望”。他也祈求着“他的女教师将来会服从他”。他希望通过征服一个老女人来作为未来追求年轻姑娘的训练,这也是文本的结尾。但“埃里卡爱年轻的男子,期待由此得到解救”,解救自己的性压抑。似乎要将自己经年累月“抑制着情欲的轧机压挤她的愿望”托付给一个年轻的男孩。
但年轻的男孩恶心着这一切,最终用殴打和强奸埃里卡的方式结束了这一切,他一边殴打一边说着这就是你要的,而埃里卡哭诉着她要的不是这样。埃里卡与克雷默尔之间横亘的就是埃里卡被母权压抑的性叙事。这是年轻的克雷默尔根本无法理解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形成了巨大的信息黑洞,使得文本在克雷默尔殴打埃里卡的叙事高潮时将性别沟通的无效性无限放大。
结尾处,埃里卡发现了克雷默尔搂着年轻的姑娘说笑着,她转身用父亲留下的万能刀片刺向了自己的肩膀,但是“刀应该刺刀她的心脏,而且在那里转动”,她捂着伤口,“她回家。她走着,慢慢加快了步伐”。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结尾。
必须予以关注的是“父亲留下的刀片”这个意象。这个刀片是在那个母女共生体的房间里仅剩的东西,这个东西一直被埃里卡保存。她试图留存一个父权意味的东西用以切割这共生体,使得自我能喘口气。刀片一 一划过埃里卡的身体:从手背——生殖器——肩膀——臆想中的心脏。她虚妄地想象着某种力量的介入能平衡被畸形关系撕扯的自我。她尝试用父亲的刀片来摧毁自我,用以抵消献给母亲的那部分自我。
文本结尾于埃里卡情感矛盾,但她居然回家了!并且竟然加快脚步!而家中只有“美洲母狮”等着她。某种意义上,宣告着埃里卡溢出母权的失败。而奥地利导演哈内克的同名电影的结尾,是埃里卡在刺伤自己后打了一辆出租车离去,并没有说去哪?
文本中似乎埃里卡承认了这样扭曲的生活已然是多年的常态,她无力改变,只能用那个刀片不断地切进自己的肉中去。文本中说这个刀片是“吉祥物”而且“在自己身体上切割是她的癖好”。这种癖好与回家的选择,文本中似乎预示了原因:“埃里卡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在隶属母亲多年之后,她绝不能再隶属于一个男人”。
埃里卡依然未能断裂与过去的联系,她的回家似乎回归到了女性的传统命运:“两性关系中永恒的他者,两性战场上的猎物,永远的权力被动者、男性欲望的对象”。女性他者的命运,弗洛伊德也解释不了,“他承认不知道男性优势的根源”。这根源弗洛伊德交给了阴茎崇拜论。
由此,埃里卡在最终的受虐信中孤注一掷地确认自我主体性的位置,她想逃脱隶属的关系,她想突破压抑的束缚,但文本结尾,作者以她回家的方式令人绝望的宣告她的尝试失败。孩子面对强势的母亲站在了弱势的一方。在孩子与母亲的争斗中,母亲以哭泣的策略总能赢得孩子的妥协。埃里卡的“母亲用哭的方式成为了胜利者”,而起因是她的女儿没有按时回家。
福柯将欲望与愉悦对立,欲望自古代尤其是基督教禁欲主义规定为具有强烈的破坏性,欲望与人格连接,约束性,控制欲望,从而形成某种(性)知识话语权,形成关于你人格的知识。很显然,母亲给埃里卡传播的正是这种知识。
母亲囚禁着她的性,但埃里卡的身体强烈地需要愉悦,在与母亲性压抑的纠缠中,“埃里卡克制了好久,直到感觉不到体内的情欲……她给身体提出费力的任务……她向自己发誓,每个人都会遵从情欲,愚昧、未开化的人甚至不怕在露天里把这事儿解决”。
克制的极致便是疯狂。埃里卡试图以自己的身体与愉悦为纲建构自己新的(性)知识—权力关系,抛弃母亲的规训。但遗憾的是,埃里卡用一封受虐信作为自己身体愉悦的支点,形成虐恋的权力关系。她似乎理解错了愉悦的内涵,或者她因为与母亲经年的共生体已经难以理解愉悦是什么了,这才是这个文本令人不安的地方。
文本中的母亲站在强势的一方,有着血缘凝结成的伦理权威,父亲的缺席导致权力的失衡,这种不幸的家庭模式有着巨大的相似性,也是社会学意义上问题家庭普遍性的缩影,它面临着与伦理权威断裂而难以寻找并建立新关系的困局。文学将这种困局放大,增强人们的不安,从而达至对这种困境的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