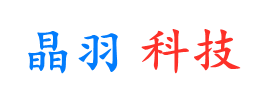涅槃炒股票(公务员能否炒股票)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IGP)
2021年12月6日,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全球繁荣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Global Prosperity(IGP)举办了“亚洲的性别与繁荣 (Gender and Prosperity in Asia)”系列讲座。这一系列共有六期,由中心副讲师何嫄组织策划,既有涵盖亚洲女性整体经济和残障状况的专题演讲,也有针对特定国家,如日本、韩国、中国、缅甸的国别讨论,旨在促进亚洲女性之间,以及欧洲与亚洲之间的理解与连结。在第四期讲座中,来自北伊利诺伊大学的世界语言与文化系副教授Tharaphi Than围绕“缅甸女性主义真的存在吗?”进行了分享。
在活动的开始,全球繁荣研究中心副讲师何嫄表示:亚洲的性别与繁荣系列讲座试图涵盖一些未被充分代表的亚洲地区,而Tharaphi Than教授关于缅甸妇女的研究令人印象深刻。
北伊利诺伊大学的世界语言与文化系副教授Tharaphi Than
Tharaphi Than教授于2014年出版的《现代缅甸的妇女》挑战了缅甸妇女自由和解放的流行观念。通过重新评估20世纪现代缅甸妇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她认为国家的历史书写框架,或者说官方历史,强调缅甸女性享有特权,因为她们展现出了强大的主体性。而实际上,缅甸妇女几乎没有经历过自由;Than教授通过研究各种公共和私人材料,探索女兵、游击队员、政治家、作家和妓女的世界,提出了这一论点。Than教授其他发表的文章有《孟拉与缅甸边疆政治》、《从黑暗土地到天堂之地: 孟拉不断变化的政治和社会景观》等。Than教授目前正致力于女性主义、异议和发生于1918年的“米骚动”(rice riot)研究。为新成立的线上联邦大学(Virtual Federal University)提供公益服务,这是一个为抵制政变的缅甸学生提供替代教育的教育门户网站。
Tharaphi Than首先指出,本次讲座旨在帮助学者与大众在缅甸背景下理解和研究女权主义。Than强调,当我们听到女权主义这个词时,我们往往会将它与西方语境下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波女权主义进行联系。女权主义者和女权学者们习惯以TA们熟悉的视角、语言和例子来寻找缅甸的女权主义或妇女运动。
许多女权主义学者试图在缅甸的背景下,找寻何种运动可以被纳入“女权主义”这一整体概念,但是TA们也因此迷失了方向。基于对西方三波女权主义的理解,女权主义学者们提出了各自的问题。基于对第一波女权主义的理解,女权主义学者们问道:“妇女是否被组织起来,还是她们自发动员了女性群体和整个国家来争取女性的投票权?”;第二波女权主义关心的,是“缅甸女性是否被允许工作?”或“缅甸的女性是否和男性获得同等的报酬?”等女性的劳动与薪酬问题;而“女性是否遭受家庭暴力?”、“妇女如何看待性解放?”等问题则属于第三波女权主义关注的范畴。但是,女权主义学者们最终无法为这些问题找到明确的答案。
在缅甸的背景下研究这些问题,很容易让女权主义学者迷失方向。这不是因为缅甸没有女权主义,而是因为女权运动并不会像西方所理解的那样,以线性或浪潮式的方式发生。换言之,缅甸女权主义运动产生的前提条件与西方语境下的背景截然不同。
Tharaphi教授接着提出了以下重要问题:一、什么是缅甸女权主义,或者说我们如何理解缅甸的女权主义?二、缅甸妇女反对的结构性压迫或父权制规范是什么?三、为什么缅甸女权主义会在2021年崛起?
缅甸女权主义的历史背景
Tharaphi教授表示,问题一与问题二相互关联,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她将引入必要的相关背景介绍。在1922年举行的缅甸初次选举中,拥有财产的妇女有权从立法委员会的103名成员中选出80名进行投票。当时,英国的纳税人有权进行投票;作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缅甸妇女被认为与英国妇女拥有相同的投票权。在英国及其他国家,女性是否有权通过自行投票或发声选举出男性或女性委员,决定了女性是否拥有自主权。但是,缅甸妇女权利的历史发展轨迹与上述权利有着巨大的不同。
在19世纪,缅甸性女担任了10%的村级行政职位,并能够拥有属于她们名下的财产。男性与女性首领的职位分别进行世袭制传承,女性可以继承女首领职位。如果在平原地区10%的女性能统治农村,在高地地区维持着母系氏族社区,那么通过投票让某人代替她们担任公职就会被视为一种倒退。在这种情况下,妇女既没有自发进行动员,也没有被动员参加选举和投票。在殖民时期的全球南方国家,女权主义运动与独立运动相互交织、密不可分。事实上,缅甸最早的妇女运动之一并不是为了争取选举权,而是围绕家庭税展开。随着英国行政机构的扩张,税收制度对农村家庭经济活动的限制日益增多,民族主义的政治组织围绕税收问题对其成员进行了动员。
妇女加入了这些政党的女性分支。她们自称为“Kumari”,参加并领导了抵制运动。她们拒绝交税,抵制包括薄纱织物和玳瑁梳在内的进口产品,因为缅甸语与英语中的“玳瑁”都包含了“leiq”一词。由于这一早期运动和“Kumari”这一名称的出现,女权运动被纳入了英属印度独立运动的范畴,“Kumari”运动也预示着缅甸妇女运动将被纳入更大的国家运动中。
在20世纪,许多国家,尤其是全球北方国家的几代妇女都没有参与独立或解放斗争的经历。与她们不同,缅甸妇女的斗争一直在民族运动的笼罩下展开。在缅甸语中,“民族”被翻译为“关于男人”或“男人的事业”,而不是“关于民族”或“关于国家”,这种语言上的疏忽凸显了为什么缅甸妇女发现她们几乎不可能发起属于自己的运动。所有人(男人和女人)都必须为国家的事业而奋斗,而女性为自己的事业奋斗则是自私且不安全的。一旦每个人都得到了解放,妇女就会得到解放。妇女的困境与每个人的困境联系在一起。这种将妇女的事业与国家的事业进行捆绑,将国家的事业称作“男人的事业”或“应该由男人领导的事业”的做法,对妇女运动和女性活动家构成了最大的挑战。女性政治领袖们学会了采取以男性或国家的事业作为自身事业的策略,以保障自己能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生存。
Kumari妇女们积极参与了Wunthanu运动(其意为热爱自己的种族),但是她们在独立斗争中的地位遭到了僧侣和男性的扭曲。受到甘地运动(Ghandian movement)的启发,Wunthanu运动中的Kumari妇女敦促女性同伴支持当地产品,并鼓励妇女生产自己的衣服。与此同时,公务员的妻子们发起了她们的精英活动:支持孤儿院,并在政府学校和办公室组织起三色堇日,即募捐活动。长期以来,宗教、文化和政治的男性领导人们决定了妇女在独立斗争和福利活动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1910年到1938年间,缅甸的女学生积极参与了学生罢工。学生们的最后一次罢工是为了声援从干旱区的油田一路游行到仰光政府办公室的石油罢工者。当石油工人进行罢工时,年轻女孩翻越过炼油厂大门的照片引发了全国的想象。与之前Kumari运动中的姐妹们一样,她们被描绘成民族运动的支持者。讽刺的是,石油工人提出的许多要求都是要求改善房屋和家属的生活条件。诸如油田工人的子女在学习时缺少照明用油等家庭困境,与殖民者对当地人的剥削联系到了一起。
因为女性被视为民族运动的支持者,所以个别女性先锋,而不是针对女性群体困境的妇女运动,被凸显了出来。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如作为第一个从牛津大学毕业的缅甸女性、曾代表国家参加1931年在伦敦举行的缅甸圆桌会议的耶盛(Daw Mya Sein),使其她不享有特权的女性黯然失色。
缅甸的妇女运动出现了两个有趣的趋势:首先,女性在独立斗争中被民族主义者定义为支持者,被殖民主义者诬陷为煽动者。她们被排在男性民族主义领袖和民族主义僧侣之后,扮演着次要角色。其次, 耶盛、昂山素季(Aung San Suu Kyi)等个别女性代表了缅甸妇女,她们被认为是女性的代表。像她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缅甸很少见,但她们吸引了过多的关注,掩盖了女性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真实地位。从历史上看,新锯浦(Shin Saw Pu)女王、女性首领和在牛津大学接受过教育的女性的存在,使“缅甸妇女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地位”的印象得以延续。
事实上,年轻的缅甸女孩和妇女比男孩和男人面临着更多困难,且无法享有平等的地位。例如,女孩的辍学率高于男孩,男性的收入高于女性。缅甸女性承担了国内收入最低的工作,其中大部分是政府部门工作。
如何理解缅甸的女权主义?
在介绍完缅甸女权主义的历史背景后,Tharaphi回到了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缅甸女权主义,我们如何在缅甸的背景下理解女权主义?缅甸女性对被描绘成女权主义者,或仅仅为女性事业而战的做法深感不安。在女医生和女军人接受采访时,她们拒绝谈及“为妇女事业工作”的话题。事实上,她们认为自己的“社会活动”(activism )在政治上是中立的。然而,女权主义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缅甸的行动主义已经完成了去政治化,这一事实也促成了男性和女性将他们的运动去政治化。
我想举两个典型例子:当我将一位在进入医学院前为穷人工作、学习政治的缅甸女医生的行为描述为激进时,她感到异常生气。女性获得关注是一种激进的行为。从耶盛到昂山素季之间,几乎再没有哪个女性能够同时领导女性和男性,开创出女性的政治生涯,或为女性开创出行动主义的道路。
第二个例子与缅甸女兵有关。她们最初被招募来建立第一支女性军队。但在战争期间,她们大多扮演配角,为士兵提供护理,并动员农村民众抗击日本人。战争结束后,她们把军装换成了平民服装,用她们自己的话说,她们已经“埋葬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女性行动主义的去政治化会使妇女沉默;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政治行动主义运动后,缅甸女性又过上了去政治化的生活。在缅甸,“男人能做和应该做的事情”与“女人能做和应该做的事情”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分界;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女性都几乎无法继续追求政治行动主义。
缅甸妇女反对的结构性压迫或父权制规范是什么?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Tharaphi教授表示:为了在缅甸背景下理解女权主义,我们需要关注妇女所处的更大的政治和社会环境。这引导我们去回答第二个问题:缅甸妇女所反对的结构性压迫或父权制规范是什么?通过研究女性如何进行自我定位,我们可以发现妇女如何在不同的结构性压迫或父权制规范下进行或组织女权主义运动。
在缅甸的政治中,女性政治行动主义的最大障碍来自于主流政治及政党政治。女性政治领袖要么选择从政界退休,要么通过参与地下共产主义运动、加入缅甸共产党或克伦民族联盟(Karen National Unions)等武装组织来进行反对派活动。在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Burma Socialist Program Party,BSPP)中,不存在任何高级别女干部;社会主义领导人的妻子倡导社会福利事业,而非女权主义运动。甚至在社会党执政初期组织的三次全国工人和农民大会上,也没有任何一位女性发言。社会党的基层成员中基本没有女性。纵观现代缅甸的五个历史时期:20世纪早期的独立运动,1948年至1962年的民主时期,1962年至1988年的缅甸社会党(BSPP)时期,1988年至2011年的军事独裁时期,以及之后的民主政府与军队事实上双头领导时期,我们发现妇女在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与军事独裁时期的参政程度最低。早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几代女性都已经退出了政治;那些希望继续参与政治的妇女转而在武装组织中找到了庇护。
在阻止妇女从政的同时,缅甸政府也限制了妇女在社会中能够担任的职业和角色。在缅甸民主时期的教育项目中(缅甸语中将该项目称为“创造新生活和教育”,但英语中则称其为“福利国家教育计划”),女教师被描述为“前线士兵”。政府大力推动女性成为手持粉笔的士兵,而不是传统军队或游击队中的战斗人员。此外,政府对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也持模糊态度,政府曾一度鼓励妇女参军,女飞行员偶尔也会出现在杂志封面上。政府使用女兵,尤其是飞行员的照片来激励年轻女孩参军,但海报上的这些女兵从未被赋予战斗角色。即使在军队中,所谓的男女平等和机会均等也只停留在杂志封面上。
缅甸政府既无法阐明女性在行政或其他部门中的职责,也无法赋予女性新的社会角色。另一方面,缅甸社会限定的性别角色也阻碍了女性的个人和集体进步。医疗保健和教育被认为是适合女性的行业,大量女性被迫在医疗保健领域的有限空间内相互竞争,这导致了女性必须获得比男性更高的分数才能被医学院录取;而工程学被认为是男人的领域,因此女性也必须拥有比男性更高的分数,才能被工程学院录取。无论以哪种方式竞争,女性都更容易遭遇失败。另一方面,家长们认为教师是有尊严的职业,适合女性,而且制服能为女性带来保护;因此他们鼓励自己的女儿成为教师。但是,此类政府工作的报酬很低;女性教师往往因为工作繁忙,难以兼顾家庭。许多大学里的女教授都因为如下两个原因保持单身,其一,她们无法用工资养活自己的家庭;其二,如果要想在学界获得更高的地位,就必须攻读一个又一个学位,这导致了她们没有时间去寻找伴侣。
在缅甸,只有大约10%的工作属于政府岗位,其余多数缅甸女性选择从事贸易,贸易也被认为是属于女性的世界。Charles F.Keyes指出:佛教认为,在世俗世界中,男人和女人可以取得不同的成就,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缅甸社会没有反对妇女从事贸易活动。佛教文化认为,男人应该花更多的时间积累功德以达到涅槃;如果可能的话,男性应该成为僧侣。但在商界的女性也会遭遇她们的“玻璃天花板”:缅甸国家级行业协会中的男性多于女性。女性可能管理着大企业,但当她们的企业被纳入行会或大企业集团时,被选为企业代表往往是男性,而非女性。尽管女性完全有能力且擅长经营企业,但由于官僚主义的阻碍和协会中男性的不信任,她们在竞选贸易或政治职位时常常受阻。
来自政治和官僚机构的阻碍,以及将这些机构贴上男性世界的标签,仍然是女性面临的最大障碍。少数有权有势的女性依靠父亲和丈夫进入了政府,这掩盖了大多数缅甸妇女缺少权力的现实。从农民到家庭主妇,普通的缅甸女性根本无法接触到政府服务与政府职位。
Pyo Let Hat和Hilary Faxon在研究中发现,由于缅甸的官僚程序非常复杂,且官方办事处对妇女并不友好,导致大多数缅甸女性农民名下没有土地所有权。官方承认的土地所有权,能够让人们获得正式的职业身份,而缺乏土地所有权导致妇女失去了农民身份。在缅甸语中,“农民”这个词是男性专属的,就像在政治上一样,在土地上劳动的女性只能担任如插秧者、除草者和收获者等辅助角色。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男性离开缅甸前往泰国,在泰国的土地上从事农业工作,女性在管理家务外逐渐担任起了更多角色。但在人们的印象中,女人不会耕地,而男人和水牛一同耕地的刻板印象仍然存在。另一方面,缅甸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从未发布过妇女耕地的海报,拒绝对妇女进行赋权。
缅甸的政府结构和官僚主义,阻碍了妇女担任掌权者。但是,缅甸的当地文化以及外部文化也对女性造成了无形的障碍。这些文化造成的障碍之一,是让男性独占了荣誉、威望和权力的概念。缅甸文化中存在一种信念,认为女性在前世没有积累足够的业力,所以女性天生就不如男性。这一信念导致了一系列行为,比如许多家庭在洗衣服时会把女性内衣和男性衣服分开,女性不能进入佛塔和宗教建筑的高层区域。缅甸的政治和宗教将女性困在“女性专属”的工作中,剥夺了她们的土地和头衔。包括军队在内的当权者,利用甚至滥用了当地的文化规范和信仰,通过讲述未经证实的Jataka或佛陀生活强化了男性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女性被赋予的卑微地位以及官方的宣传帮助男性巩固了在治理上的权力。这种阴险的、政治和宗教上的双重游戏让女性难以招架。
除此之外,西方对缅甸的女权主义以及女权运动方法的长期干预带来了危险的后果。缅甸的女权主义不是显而易见的。在2010年到2020年间,当外界开始为女性运动提供资金时,许多女性活动家感到了压力,她们必须获得曝光,才能使自己的工作被视为女权主义运动或被划入性别行动主义。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加入缅甸民族武装组织或共产党,以及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本世纪初在缅泰边境地区的活动人士不同,许多女性活动家在城市政治中找到了立足之地。但是,除了民族武装组织下属的妇女组织,多数妇女组织都把议会制度改革列为运动的最优先事项。在2010年和2015年的选举后,军方将权力移交给文职政府,缅甸的社会文化成为了变革最为明显的障碍。另一方面,反家庭暴力运动成为了凝聚许多妇女组织的共同事业;对于那些无法成为全职活动家的人们而言,为期16天的活动为她们提供了参与小范围女性主义运动的机会。从政府到社区,缅甸社会的各级层面都广泛讨论了关于性别暴力的报告,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步骤。
到2010年代末,阴道独白,甚至女权主义这个词变得更为缅甸女性所接受,白丝带运动与Metoo运动在缅甸兴起。但这些以城市为基础、由非政府组织推动的团体化性别行动主义运动,与民族武装组织的“妇女之翼”运动之间是分离的。“妇女之翼”运动不断指出,文职政府下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军事统治,这使得妇女无法过上稳定生活。2010年代的缅甸妇女运动或女权主义运动被归入了普世的妇女及女权主义运动,这些运动争取的性别平等围绕着“摆脱家庭暴力”和“增加政治中的妇女代表”等目标展开。这些运动强调个人自由和个人成就,而女性的集体解放则被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且无法在短期内实现。此外,2010年代的女性运动无法为农民或服装工人运动提供支持;在后面这些运动中,女性在为争取自己的土地权利和获得公平薪酬而奋斗。
总结而言,缅甸的政治问题、官僚主义和基于特定“女性主义”的行动主义运动,削弱了渴望围绕土地权利、公平薪酬等非女性问题来争取集体解放的女性活动家的力量。全球或西方女权主义的狭隘视野,只能制度化地看到投票权、性解放、同工同酬等议题,而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则不愿意支持缺乏这些标签的本土运动。当女权主义者将女性运动的目标定为争取自身权利,并试图将其从主要的民族运动中独立时,组织之间就会迅速产生紧张关系。
为什么缅甸女权主义会在2021年崛起?
Tharaphi教授在第四部分解释了缅甸女权主义在2021年崛起的原因。在政变中出现了“跨越激进政治”的政治形势,该形式偏离了主流、大众或多数人支持的精英政治。政变无疑证明了军队和领导党之间的双头局面无法运作。在突然开放的政治空间中,激进的声音和政治脱颖而出,占据了中心位置。缅甸语境下的女权主义是激进的政治,因为它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妇女不迎来解放,社会就不会迎来解放。尽管充满偶然性,但是在缅甸现代历史上,2021年的革命首次正视了妇女问题和呼吁的重要性。
在社交媒体和即时新闻的时代,从城市到农村、平原到高地,妇女的政治参与和行动引人注目,且不加过滤、未被审查。各式各样的女性行动主义,从在市中心升起女性纱笼;高喊着“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但不要强奸我”的口号进行游行;到妇女谨慎地准备爆炸材料;城市妇女以战争难民的身份抱着小孩示威,以引起人们对少数民族的关注,这些行为打消了“女性是否应该参与政治”这一问题。破裂的政治让女权主义的存在显露无遗。
有三个群体的妇女抗议者最为引人注目。首先,是身为公务员的女性抗议者。缅甸10%的人口是公职人员,其中的教育工作者和医生多为女性。她们的罢工使政府服务陷入停滞。第二类,是身处农村的女性抗议者。农村妇女和少数民族妇女可能不像城市里的抗议者那样引人注目;她们中一些人,特别是那些逃离激烈冲突的人,可能不会选择上街抗议,但她们积极支持革命,在经济上为武装分子提供资助,为他们提供庇护,更重要的是给予抵抗战士们道义上的勇气,并支持他们的事业。第三类,是女性战士和女性顾问。修女、教师、教授、人类学家、法律专业人士在前线战斗的同时,也在教育着战区的儿童。
从反政变抵抗运动到革命运动的迅速演变,凸显了激进和边缘政治的重要性。缅甸的女权主义一直存在,但外界只能看到西方能理解的女权主义。事实和隐喻双重意义上的边缘政治,即由少数族裔拥护的政治走向了中心,该群体不断强调父权制军民国家的内在暴力。女权主义在其中找到了同盟,因为女权主义本身一直属于边缘政治。
军事化的社会,而不是个人暴力,催生出了制度性暴力;它们相互繁殖,为彼此提供保护。来自掸族、克伦族、克钦族和罗兴亚族的少数民族女性活动家们呼吁停止针对妇女的暴力,“停止将强奸作为一种战争武器”一直是她们运动的核心口号。2021 年,揭露缅甸军队手中少数民族妇女的困境,以提高人们对侵害女性的暴力行为的认识已经成为16天白丝带运动的目标。女性行动主义、性别平等运动与女权主义一起取得了无法衡量的巨大进步,女权主义者不再被指责为“对自身女性身份缺乏安全感”的愤怒女性。
在 2021年的革命中,国家政治已经与女性政治建立了联系,为女性政治开辟了空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一直在讨论如何制定目标,同时确保革命目标必须反映最受压迫的群体,包括妇女和LGBTQ群体以及包括罗兴亚人在内所有少数群体的需求。衡量革命成功的标准,不是看它为特权阶级和大多数人谋取到了怎样的权益,而是看它为社会中最没有特权和最受压迫者争取到了怎样的成果。
在革命中,被忽视群体获得的关注,以及被沉默群体的发声,给人们带来了社会集体进步的希望。经历了苦难和流血后,缅甸获得了一些希望。在缅甸的女权主义的历史中,从前个人是非政治的,更确切地说,个人的没有成为,也不能成为政治的一部分。但政变改变了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保持活跃的女性和LGBTQ群体抓住了政治断裂的机会,以其诉求为中心,强调了基于性别的系统性压迫。整个缅甸社会也逐渐认识到:一场不能同时解决这些系统性压迫的革命,将会是一场不完整的革命。
责任编辑:龚思量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