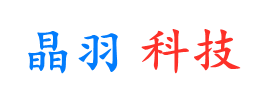实验电影好看吗
2009年,詹姆斯·班宁首映了《鲁尔区》,这是他在近40年完全用16毫米制作的作品之后的第一部数字电影。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尾巴上,在经历了二十多年模拟视频格式和数字视频格式在实验电影制作领域缓慢扩散的痛苦后,《鲁尔区》似乎标志着该技术被广泛接受的转折点。
毕竟,如果班宁能接受数字,我们为什么不能呢?

在2019年,电影与视频之争似乎有些离奇,这并不是因为《鲁尔区》或任何其他电影将我们带入了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在那里,我们所接触到的一切都是平面上被照亮的像素,而是因为,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赛璐璐在实验电影场景中仍然像在数字电影场景中一样重要。这两者甚至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伙伴。

正如评论家和学者Leo Goldsmith所指出的,一些艺术家正在寻找富有成效的方式来整合两种媒介。
Goldsmith引用黛博拉·斯特拉特曼(Deborah Stratman)和本·里弗斯的作品(Ben Rivers)说,这些艺术家和其他艺术家正越来越多地将电影和视频作为“可以在两者之间进行切换或中间融合的选择”,从而产生不可思议的审美对象,以挑衅的方式玩弄物质的概念。

你很可能在画廊和电影院看到这些作品,这只是近年来“艺术家的移动影像”一词被采用的一个原因,用来描述由不同创意和文化背景的电影制作人和视觉艺术家在多种背景下制作的电影和视频作品。

正如吉纳维芙·岳(Genevieve Yue)在2015年为《电影评论》(Film Comment)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艺术家经营的电影实验室的兴起,是维持赛璐珞在实验电影制作界存在的一个关键因素。
她写道:“90年代早期,只有少数几个合作经营的独立实验室,大多在法国,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由30多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网络。”

五年后,这些组织不仅继续为新一代的艺术家提供拍摄电影的机会,而且,正如Goldsmith指出的那样,这也为电影制作人提供了资源,以建立“一种为战略目的在不同媒介之间或跨媒介工作的实践”。

旧金山电影资料馆(San Francisco Cinematheque)的艺术总监史蒂夫·波尔塔和一年一度的实验电影十字路口电影节(Crossroads festival)的艺术总监呼应了这些观点:“这些团体的后历史、后启示录、以社区为中心和非个体的氛围真的是这十年最大的新闻。”

事实上,这些广泛存在的草根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实验性电影界的重要分散化,也使电影制作人越来越倾向于从边缘地区寻找新的声音。
2010年的《Avant-Garde》与我们今天可能认识的景象几乎完全不同,它不是通过几十年的本地化话语,而是通过互联互通、技术民主化和更大的社会包容性大步发展而形成的。

随着肤色的转变,美学也发生了转变。非小说(或者人们可以称之为对现实的创造性思考)是这十年的主导模式,哈佛大学感官人种学实验室(SEL)的崛起为先声。
这是一个校园跨学科的人类学媒体艺术中心,由声音艺术家恩斯特·卡雷尔(Ernst Karel)和电影制作人吕西安·卡斯坦因-泰勒创立。

虽然实验室在21世纪的后期首次取得进展,直到2012年的《利维坦》才在更广泛的电影意识中确立了SEL的风格和概念上的创新,这是由卡斯坦因-泰勒和法国导演(也是人类学家)维瑞娜·帕拉韦尔用GoPro相机拍摄的航海民族志的杰出之作。

继《利维坦》之后,这部电影将直接电影和抽象表现主义激进地融合在一起,并在这十年中的另一项主要成就——斯蒂芬妮·斯普莱和帕乔·韦莱斯的《通往圣山》(2013)中运用观察技巧,可以在很多其他不相关的实验类和纪录片类作品中找到。

就像艺术家运营的实验室和工作室一样,SEL被证明是年轻电影制片人的重要孵化器,他们有着广泛的创意和政治兴趣,为制作者提供了大量可供发掘的新鲜而有活力的人才。
对于美国动画师茱迪·麦克(《大怪扎》)来说,可以说是过去十年中最令人激动的活动影像艺术家,这些策展趋势是双向的。

她说:“一方面,我很高兴策展人正在关注来自不同背景的年轻电影人。另一方面,实验电影的‘品味’和精英性质与我们所追求的真正社会发展背道而驰。所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波尔塔也注意到(事实上,他对)策展人对“以清晰、明确的术语呈现信息的新闻和信息为基础的作品”越来越感兴趣,这明显背离了“先锋派的幻想、感官、狂喜的野心和成就”。

在一个很大程度上制度化的领域中,大多数转变都需要考虑相互冲突的力量和伴随而来的争议,其中只有一些是议程驱动的。
作为TIFF的Wavelengths项目的负责人,Andréa Picard一直在新旧趋势之间取得令人羡慕的平衡,根据她的说法,策展并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冒险,也是一种实践。

她说:“空间限制,整体环境,财政支持,这些因素经常被忽视,并以关键的方式影响着电影节的制作。”
举例来说,人们可能会注意到Picard对实验性3D电影(尤其是布莱克·威廉姆斯的立体电影)的持续奉献,她能够在TIFF的贝尔灯箱影院中容纳这项技术,但许多其他影院却无法支持,这纯粹是后勤问题,甚至没有开始考虑年龄、种族或性别的因素。

因此,值得重申的是,看什么电影和被谁看是一个多方面的问题。在担任安娜堡电影节的首席策划人期间,大卫·丁内尔(David Dinnell)支持了许多艺术家的早期电影;
2016年,他突然退出该组织,这是十年来最具争议的事件之一,也进一步证明了官僚机构并不关心艺术或创造力的问题。

但当新事物取代旧事物时,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这些发展,还要考虑它们告诉我们媒介与变化之间的矛盾和日益紧迫的关系。
正如评论家迈克尔·西金斯基(Michael Sicinski)说的那样:“我们倾向于在主流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抛弃残存的东西,与新兴的东西保持距离。”

至于新兴的可能是什么,西金斯基指出了在TikTok和Snapchat等短片移动视频应用中探索的新的视觉前沿,后者为瑞士裔美国艺术家Christian Marclay提供了数百个片段,他用来组装他的新的声音故事装置——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来源,数字图像作为我们最普遍的货币持续存在。

换句话说,潜在的竞争环境将继续保持水平——或者如麦克所言:“没有人是天才。每个人都是天才。作者身份已死。社区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