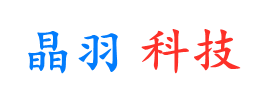《花城》2017年3期刊发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李佩甫新作,揭示贪腐有痕,只是自己不知
《花城》过去被称为中国文学期刊四大名旦之一。另外三个旦,分别是《十月》、《当代》、《收获》。
凭着当年自己朦胧的印象,觉得四个名旦,各有千秋,但也各有风格。《当代》古板有余,文采不足,但时有黄钟大吕作品。我记得《大上海沉没》就发在《当代》之上,奇怪的是,从地域来看,更应该刊在《收获》上啊。当年到上海福建路旧书店里买回了很多旧杂志,其中就有两本是刊有连载《大上海沉没》小说的《当代》。前一段时间,还把它翻出来读了一下,读到一半,就碰到字体太小的瓶颈,而且错别字离奇的多,所以,读了一半就把它搁在那儿了。而跷蹊的是,同样在《收获》上,反映广东商业改革的小说《商界》也竟然是刊在这个刊物上,而没有发表在《花城》上。发现当年自己购买的旧期刊,都是有意选择刊有长篇小说的旧刊。
《收获》杂志,工整稳妥,执着于古怪的文字,不管你懂不懂,它能够把一部部小说排列得整整齐齐,煞有介事。就像《故事会》一样,它有一种上海杂志的特有的严谨风格,把什么都能够做到极致,但明明上海这一个大城市涌动着毛毛糙糙的躁动,然而做杂志却能做出如此细腻、冷静的考究,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总体觉得《收获》不会在可读性上给你一点安慰。
《十月》觉得最为通透,它热情奔发,内心简单,但文字却能奔涌着一股热情,看起来,有一种炽热的情怀。
《花城》呢,很难想象得到,它是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它里面没有南方城市的那种灯红酒绿的喧嚣,反而能够乐此不疲地沉静在乡野与偏僻之处,执着于文字本身所焕发出的力量。
《花城》2017年第3期,一册在手,依然让人感到一种清新脱俗之感。孔子曾经说过,久不梦周公了,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读者来说,也算是“久不读文学杂志”了,但一册文学期刊在手,还是能够激起我们心中的那份毛毛糙糙的激动感,好像一本杂志让我们夜不能寐的岁月再度重现在眼前。
这一期杂志上刊有作家李佩甫所著的长篇小说《平原客》。李佩甫不久之前刚刚以《生命册》获得茅盾文学奖,正处于文学创作的巅峰,这一部小说很令人期待。
与《生命册》一样,李佩甫在这部小说里,再次让乡村中人在城市的漩涡里展现灵与肉的激烈撞击。相比于《生命册》里的由第一人称的稍稍显得局限的视角,在《平原客》里,李佩甫恢复了全能全知的视角,展示了从农村里走到城市里的官场中人,是如何在城市里的巨大欲望冲击面前,一步步堕入深渊,万劫不复的。
乡村与城市的撞击,一直是李佩甫作品中的主题,而这一主题,如果追溯起来,可以说是出身农家子弟的作家都喜欢选择的一个主题。如《生命册》里,主体叙述者的玩世不恭的叙述语调,依稀能够让我们想起莫言在《丰乳肥臀》里的自我调侃,同样也会想到路遥在《人生》里确定的农村与城市对对碰无一幸免的结局:被城市撞得头破血流,最终还需回到乡村寻求慰藉。
在《平原客》里,我们可以看到李佩甫一直以一种散点状的结构,娓娓道来,它开始的描写,显得宏大而松散,作者的叙事口吻,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任意地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无原则的跳跃,在这种叙事笔法下,小说里推出了两个从农村里走出的官员的人生经历,这就是小说里的市级干部刘金鼎与省级干部李德林。
作者就像没有聚焦目标的镜头,随意地扫来扫去,先瞄准了刘金鼎,然后,对准了一个真正的核心人物李德林。就像《红楼梦》里,要认识荣国府,必须有一个刘姥姥,她是一个触发点,借助于这么一个地位稍小的人物,才能感知到荣国府里的大千世界。同样,在《平原客》中,小说里先推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花匠刘全有,然后,描写了他的儿子刘金鼎如何求学、求人、求生的经历,由此,而引出了那个看起来似乎只是小说背景的李德林。这个在小说里描写的开初在小人物眼里属于大人物的李德林,也由此展开了他的情感与欲望世界,并导致了整个小说后半部分的急转直下,这就是堕落的急转直下。
城市生活给予乡村一员的不适,在《生命册》里有淋漓的表现,相对而言,《生命册》里并没有过山车般的急转直下、一泻千里的结局,而《平原客》却在小说体量过半之后,突然之间踏上了一个加速向前发展的平台,不可抗拒地向滑向了那不可扼止跌落的结局。《生命册》里表现的是乡村在城市里受阻的问题,而《平原客》更为残酷地揭示了:乡村会在城市里堕落。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小说里给人的一种沉重的命题。小说里最初以侧影的方式出现的李德林给人的印象相当的正面,他出身农家,朴素诚实,亲民随和,严于律已,工作勤勉,一点没有架子,官至副省长,并且有望进入中央领导的行列,可以说,李德林是我们在现实中难以碰到的一个好官,为什么却最终堕落为杀人犯,以命偿命?这里究竟哪一点犯了错?
可能李德林本人也对此百思不得其解。他有一句口头禅:“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这—句话,也是小说的篇首作了引用,可用这句话对于理解小说至关重要。这句话说的是:大自然的变化,看起来是没有明显的标志的,也不会给人一个明确的告示,但就在那个沉默的瞬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这句话,实际上喻示着:堕落看起来是没有迹象的,但那只不过是自己不知道而已。
《平原客》在整体的文字书写中,并没有盲点,把李德林的所有的秘密,都平铺在读者面前,但是,他为什么堕落成死囚,小说里并没有一字直接告诉我们。而从这里,我们正可以看出李佩甫的写作风格。从文字上来说,李佩甫的文学描写是一种如实的再现的鸟瞰式风格,不断地切换叙述视角,以一种上帝的视角,展现出事件的全程面目。这种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在先锋叙事语境下,显然并不算上是新潮。但问题是,李佩甫用他无所不能的全能视角,打造出来的社会现实,没有空档,没有盲点,却给人一种不可思议的荒诞感,一种抽象式的隐喻式的内涵,就不能不觉得李佩甫作品在一种表层的现实语境之上,还有一种总揽一切的意象式空间。这也是李佩甫的小说能够以小见大、以一隅见全局、以具体见宏观的特有意蕴的原因。之前的作者的长篇小说创作,就被认为是通过乡村一隅的现实描绘,映射的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矛盾纠葛的大局图谱,折射出的是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深层内幕,这无疑是一个作家在构思框架之上注入了自己更为复杂、更为深沉、更具有统筹力度的深层设计,才使得小说的局部是透明明晰的,但在合成之后,却形成了一道道浑沌的胶着的厚度与深度。
李德林的堕落之途,他的第一任妻子看的一清二楚。当年,她看重他的技术人员身份,主动下嫁,但是,新婚第一天,她就领受了乡民们闹新房的凌辱,那些和善的乡亲们,在黑灯瞎火之下,“摸她的乳房,捏她的屁股,拧她的大腿”,令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之后,那些乡村来的亲戚,不拘小节,把家里作踏得不成样子。实际上,乡村中人,走进城市,都面临着一个是适应城市还是屈就乡村的矛盾。妻子不能容忍李德林身上的乡土痕迹,坚决地与他分手了,分手之际,留下一句话:“你要想真正成为一个科学家。就要切断‘脐带’,切断你与家乡的一切联系。不然,他们会毁了你的。”(P34)。
这就是中国文学始终在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孕育了城市的乡村,在城市能够自立的时候,却最终必须面临着抛弃的命运?李佩甫在小说里提出了一个与路遥时代迥然不同的审视乡村视角,在李佩甫的笔下,绝对没有路遥在《人生》中陈述的乡村是城市的坚实后盾的理念,李佩甫一直反思着乡村的负面价值与意识形态,而这种解剖的力度,在《平原客》中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看出,走进城市的乡村中人,放弃了土地的包袱,可以说在精神上,更没有顾忌,更没有立场,在他们的面前,唯一要做的,就是如何生存与立足。这种简单的诉求,使他们在步入城市之后,根本无视城市的规则,而肆意地展示他们的无所不为的钻营性。在《平原客》里,我们可以从小说里的引子式的人物刘金鼎身上鲜明地看到他的竭力在城市里打洞的乡村意志。他是花匠的儿子,小时候,他上的第一节课,就是认识到关系的重要,后来他高考失利,是父亲求哥哥拜姐姐,找到关系,把他送上了大学。之后,他巧遇校长,凭借这一关系,他青云直上,从县级到市级,成了当地炙手可热的高官。之后,他成了副省长李德林的知音与后盾,为他拉帮结派,营造基地,甚至介绍老婆,他与李德林都是农家子弟,一旦攻入城市,他们必然选择抱团取暖,联手出击,扩大在城市里的战果与营盘。他们是乡村的佼佼者,但要在城市里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不择手段,动用能够存活下去并且繁衍下去的所有的资源。而刘金鼎这种动机背景里,在小说里交待,还有着中国文化的深层积淀滋养。小说里在描写刘金鼎萌生出为省长大人建立“据点”时联想到:“当了国家领导人之后,老师手下得有个亲信班子,有一些靠得住的人才行。史书上说,当年一个小小的‘平原君’就有三千门客,那一个个都是死士呀……何况是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呢?”(P73)。这一段看起来明白如画,但背后的玄机却耐人寻味。作者在小说里表现了“中原客”这一个庞大的部落体系,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原地带恰恰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因此,在中原的乡间更保真着中国文化的一些传统与精髓,而这种精髓,以一种民众的朴实的形态冲击的时候,沉滓泛起的就是中国文化的更为复杂的深层积淀。
李德林的跌入深谷的第一步,就是在于他的家乡观念。他的前妻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而李德林当初对刘金鼎善意的帮助,最终却成了自己毁灭的导火线,作者的深层意图,显然是折射出高密度地蕴含着中国文化传承的乡村文化,带着一种有毒的力量,在一步步地毒害着李德林这样的高官的心灵。
之后,刘金鼎又用女人攻下了李德林的内心世界。在李德林离婚后,刘金鼎为他选择了一个看起来本分的女人,但是小说里也提到了她的眼神里的执拗或者叫坚韧的东西,而正是这种东西,日后反过来压制了她身上最初的那种勤劳、朴实、本份,而成为一种恶。这个乡村女人一旦成为副省长夫人之后,很快认识到权力的巨大价值,无师自通地借助丈夫的权力指挥捧,谋取利益,开始了一个本来是本份的女人堕落的第一步。小说里写道:“有时候,‘尊重’是一剂慢性毒药,当一个人习惯被‘尊重‘的时候,她就危险了。”(P45)。一个乡村女人,没有底蕴,根本无力应对权力带来的巨大诱惑,反而为了享用这种权利带来的巨大好处,她竟然反过来去反制居于“权力之源”地位的丈夫,导致丈夫无法容忍,不得不运用他的关系网,把她给除掉了。
这样小说的下半部分就是一场破案的急如星火的动作戏。而在这一过程中,作者浓缩了我们在各类高官落马案件中耳熟能详的桥段,赋予了小说里的人物的身上,因此,小说里相对简单化的人物动机上,却包孕了至今依然迷雾重重的口耳相传高官落马的种种戏剧性因素,在小说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高官杀妻,使我们联想到发生在高级官员家里的杀人案;被抛弃的前妻举报丈夫(小说里的谢之长的妻子梁玉芬揭露丈夫,揭开了迷案的盖子),使我们想到贪官落马背后的妻子举报因素;一声正气的公安局长赫连东山,却受到了同样的力量的狙击(小说里这一段颇耐人寻味,他查破了案子,但自己反受到审查,而他无力面对的是,对付他的人,正采用他当初对付别人的铁手腕);反贪反腐过程中,上级出于保护考量而有意为之的对破案结果的干预(如小说里提到的查案到此为止)。这些真实发生的官场拍案惊奇,被作者天衣无缝地缝贴到小说里的人物命运中去,便产生了一种超脱于前台人物的魔幻风格,令我们觉得,小说里相对简单的人物构造,却还有更为复杂的更有纵深的难以考究的心理因素,显然,我们都知道,真实发生的动机,远不是小说里描写的这么单纯,即使如李德林的杀妻动机,小说里深入到床闱之下,对李德林受到妻子凌辱的细节,都交待的一清二楚,而我们显然可以想象得到的是,真实情境下发生的这些贪官们的幕后的作为,要比小说里的人物设定更为复杂得多,但作者就是凭借着由自己提供的简单化的人物勾勒,再粘贴上更为繁复的贪官幕后中透露出的一星半点烛影斧光,便生成了小说里的一个亦真亦假、似真似幻的魔幻般的境界。这就是李佩甫在小说构思上的高明,作者能够超越文本之上的高一层次的意境之上,抒写出社会现实的魔幻风格与荒诞意境。从这一点上,《平原客》可以说起于平凡叙事,但终于影射意象,使小说的整个思想空间扩大与延伸了数倍体量,远远高于文字提供的薄薄的含量。
相对于《平原客》的有限的文字蕴含与巨大的延拓空间,本期中的短篇小说《祖先与小丑》未免显得有一些平淡,整个小说只是以写实的手段,交待父亲的逝世与自己孩子诞生的过程断片,意图通过生命的终结与诞生来考察人生的延续与生存的价值问题,作者把小说的“眼”建构在生与死的对立这一矛盾的价值冲撞上,以此作为短篇小说能够立足的支撑点,基本完成了一篇短篇小说能够站得胜脚的谋篇布局问题。而在“花城关注”栏目里,重点考察了85后创作的小说与诗歌,体现出杂志意图对新生代读者的迎合意图。总体来说,本期《花城》以黄钟大吕《平原客》布局,撑起了这期刊物的骨架与内质,也让本期刊物留给读者一种厚重与饱满之感。